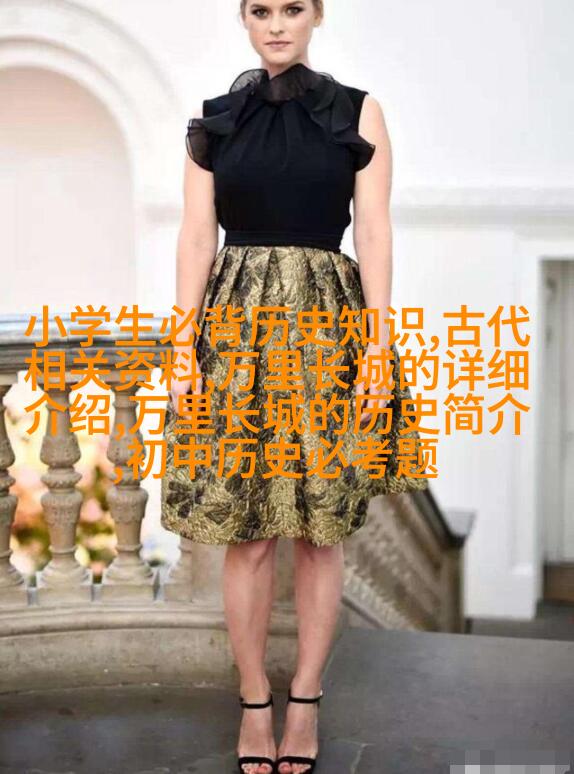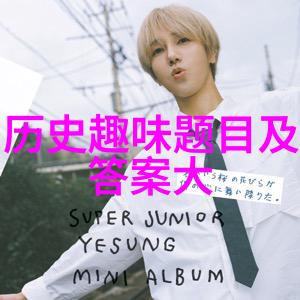我记得古代的图书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其中,官府刻书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佛道经典;私人刻书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级读物;与其他两种形式不同的是,书坊刻书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进行印本书的生产和销售。明朝之后,書坊生產的圖書種類多、數量大、流傳廣泛,在當時圖書出版業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為舊時市民文化的一个缩影。

我知道中国古代書坊出現於唐朝,這是因為科舉制度的發展,讀書人對書的需求量逐漸增加。那時,書坊刻書內容非常豐富,有儒家經典、文集、雜記、占卜書籍等。到了宋朝,圖書館逐漸由印刷技術取代了手抄方式,圖書館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加速了商業化進程,而張择端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的店鋪招牌就標註着“書房”二字。那時出現了京城汴梁、三江浙閩各自擁有一個刻版中心,其中建安余氏與臨安陳氏最為聞名。
我還記得南宋詩人劉克莊赠友人的詩云:“陳侯生長繁華地,却似芸居自沐薰。炼句岂非林處士,鬻學莫非穆參軍。雨檐兀坐忘春去,雪屋清談至夜分。何日我閑君閉肢,不僅能在市區開設一間賣本子的店子,更能悠然自得,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結束我的事業,与朋友一起乘船遊覽北山之景。”這首詩描繪了一位叫陳起的人在繁華都市中開了一間賣本子的店子,他不僅賺錢,而且能夠享受生活和心靈上的滿足。

到了明朝,我們看到那些市民通過經商等途徑快速積累財富後,不僅需要大量奢侈品來充實生活,更需要通俗文学来娱乐身心。当时一些主张迎合这样的社会形势,他们推出了很多流传甚广的通俗读物。在这些通俗读物中,从组稿到印刷、出版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我还记得凌濛初编著的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系列,它们极受当时读者欢迎,这些作品都源于他看过冯梦龙所写《三言》的故事后受到启发,并在“肆中人的怂恿下”,将各种故事收集起来编撰而成。而“肆中人”指的是那些从事图书交易的人,因此可以说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明朝经典读物《拍案惊奇》系列问世。
此外,《拍案惊奇》的成功后,又有人請求再次發行,所以凌濛初又寫了一篇序言稱:“贾人一试而效谋再试之。”可見,那时候這些通俗讀物的发行完全是迎合市場需求來進行運作的一部分。此外,《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也是從同樣背景下走向我們眼前的,一部经过众多学者整理并修订后的版本,该版本序言提到,“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说明这类作品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最终能够深入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认识。这让我更加明白,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渴望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同时也期待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群辛勤工作于图书出版业中的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打造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欣赏到的宝贵文献遗产。在那个充满变革与发展的大环境里,每一次文字记录都是时代精神的一抹光芒,是人们智慧结晶的一份珍贵财富。不仅如此,这些文艺作品更是一扇窗,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长河,对过去世界有一个更为深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那段历史如同自然界里的风景一般真实而迷幻,让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无法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依旧会被它们吸引,被它们带回那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情怀世界之所以如此魅力无穷。在那里,每个字每句话都承载着前辈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于现在苦难生活的小小慰藉,以及对于未来可能发生一切事情的小小准备。但愿我们的追寻永远不会停歇,因为就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亮色,为自己织就更多回忆。而所有这一切,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却默默付出的功夫,就没有今日之璀璨。如果没有那座座巨大的图库,没有那些默默服务于人类知识传递的大师们,那么这里将只剩下空荡荡的一个空间,只剩下零星几片落叶,只剩下往昔曾经存在但已消逝的声音。如果没有他们,那么整个宇宙都会失去光彩,就像缺少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枯萎无花。如果没有他们,那么我们便只能活在黑暗之中,用盲目的双眼触摸周围的事物,用盲目的耳朵聆听周围的声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以开放的手掌拥抱一切,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也才能真正意义上的了解这个世界及其居民——你我他——以及这个宇宙及其所有生命体——它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