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今1000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农人的数量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和“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每个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加的人口压力。于是,这些超出需求范围之外的人民被迫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并建立起新的村庄。而当这些区域有一些边缘地带不适宜移民开发时,当地居民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以保证自己生存下来。非洲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曾广泛分布于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的群体,被分别挤到了茂密丛林地带和荒凉沙漠地区。
北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曾广泛分布于操绒绔尼语印第安食物采集者的群体,由于普韦布洛农人们排挤,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见图"狩猎者的后撤"和"农人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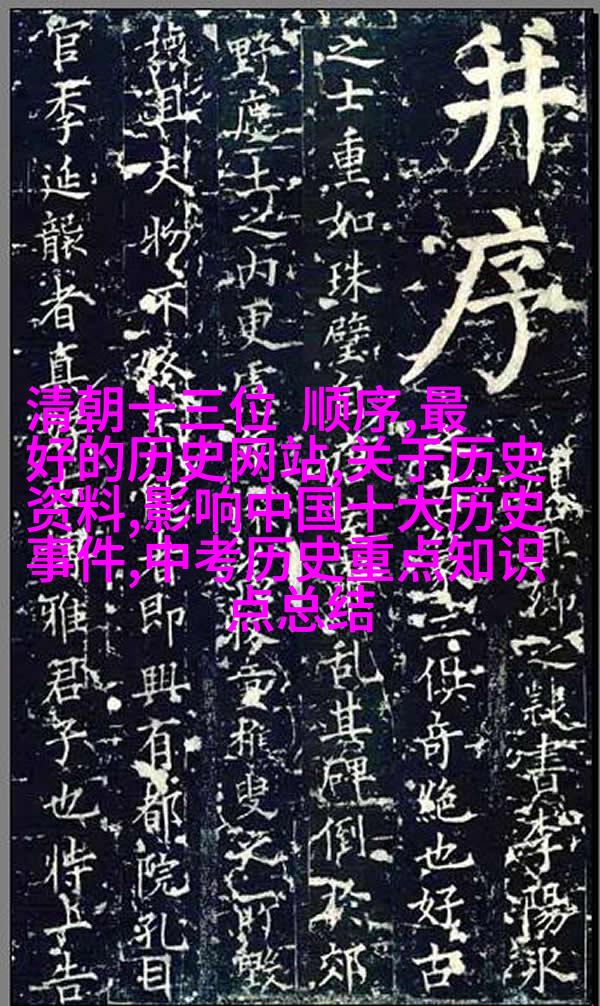
除了共生关系,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情形,即共存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仍然盛行的情形便是一个例子。那里的俾格米人向耕种土地黑人的提供肉类、蜂蜜及其他森林产物,再从黑人那里接受作为报答谷粒或铁制武器。这两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同时保持各自特点。
最常见的是移民与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发生通婚融合。当再次形成压力时,这些混血儿居民便向新的地方迁移,与那里的当地居民通婚,并逐渐融合。这就这样传播了农业技术以及农作物,而那些最后将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蒙古种人才成为其类型完全不同于创始者的混合品种。此外,不同地域间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发现原发来源于中东的小麦、牛、轮子及犁的事实反映出这项技术最终由纯粹蒙古种人才完成这一壮举。而且,当这项技术被引入欧洲西方及非洲南部大草原时,又发生了一系列迁徙以及异族通婚事件今天存在在赞比亚南部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就是一个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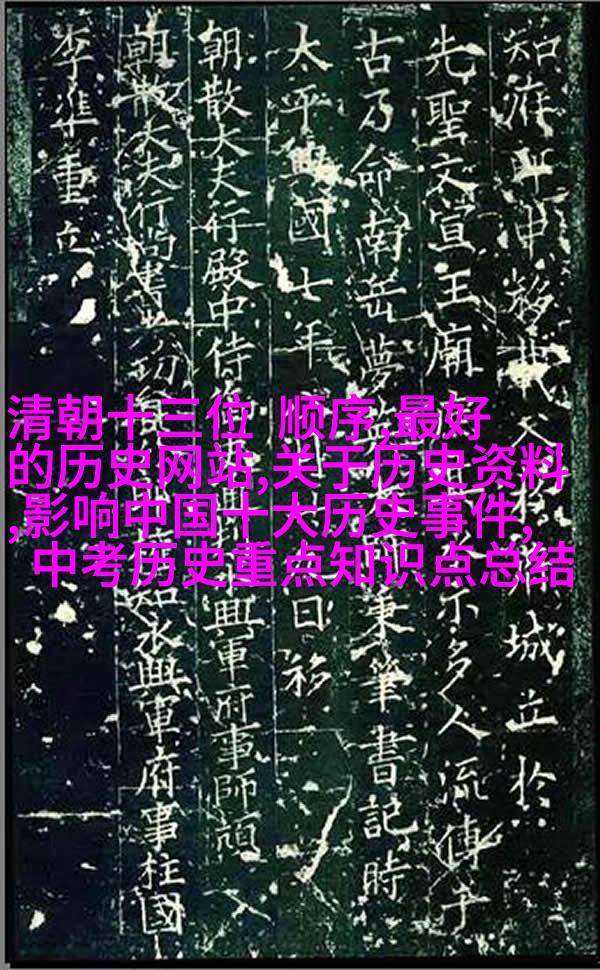
一系列迁移使得全球范围内所有地区都接受了这一变化,最终结果是,只剩下公元1O00年的15000名狩猎者占据全体人类只占1%左右比例。一系列职业转变转而导致了全球性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对各种生物学上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如早期六大主要种族(高加索種、蒙古種、高加索種+蒙古種+澳大利亞原住民+黑色+俾格米-撒哈拉以南非洲-東亞)之间基本平衡遭受剧烈扭曲,此趋势极有利于进行耕作生活方式,如高加索種、中东與農業技術發源點相關,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亞地區,這兩個區域對於進行農業生活方式具有巨大的好處,並對過渔獵採集生活方式持續擴張,使他們成為今日依據數量壓倒其他任何單一生物學類別生命體。他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優勢因此根植於今日,他們的地位從此難以動搖——為我們今日見證到的現狀奠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影響,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專注於耕作事业及其伴隨之農業成果的一個時代,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世界将会截然不同,因为没有这种长期稳定的优势支持,它们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多样化多样的文化形式;如果没有它们,将无法解释为何他们能支配地球表面那么大的部分;如果没有它们,将无法解释为何他们拥有那么多丰富资源;如果没有它们,将无法解释为何他们拥有那么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它们,将无法解释为何他们拥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力量;如果没有它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似乎无所不能。但即使如此,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回头去探究那个奇妙年代,我们一定会惊叹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小小的手指触碰地球表面的某个角落,可以改变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