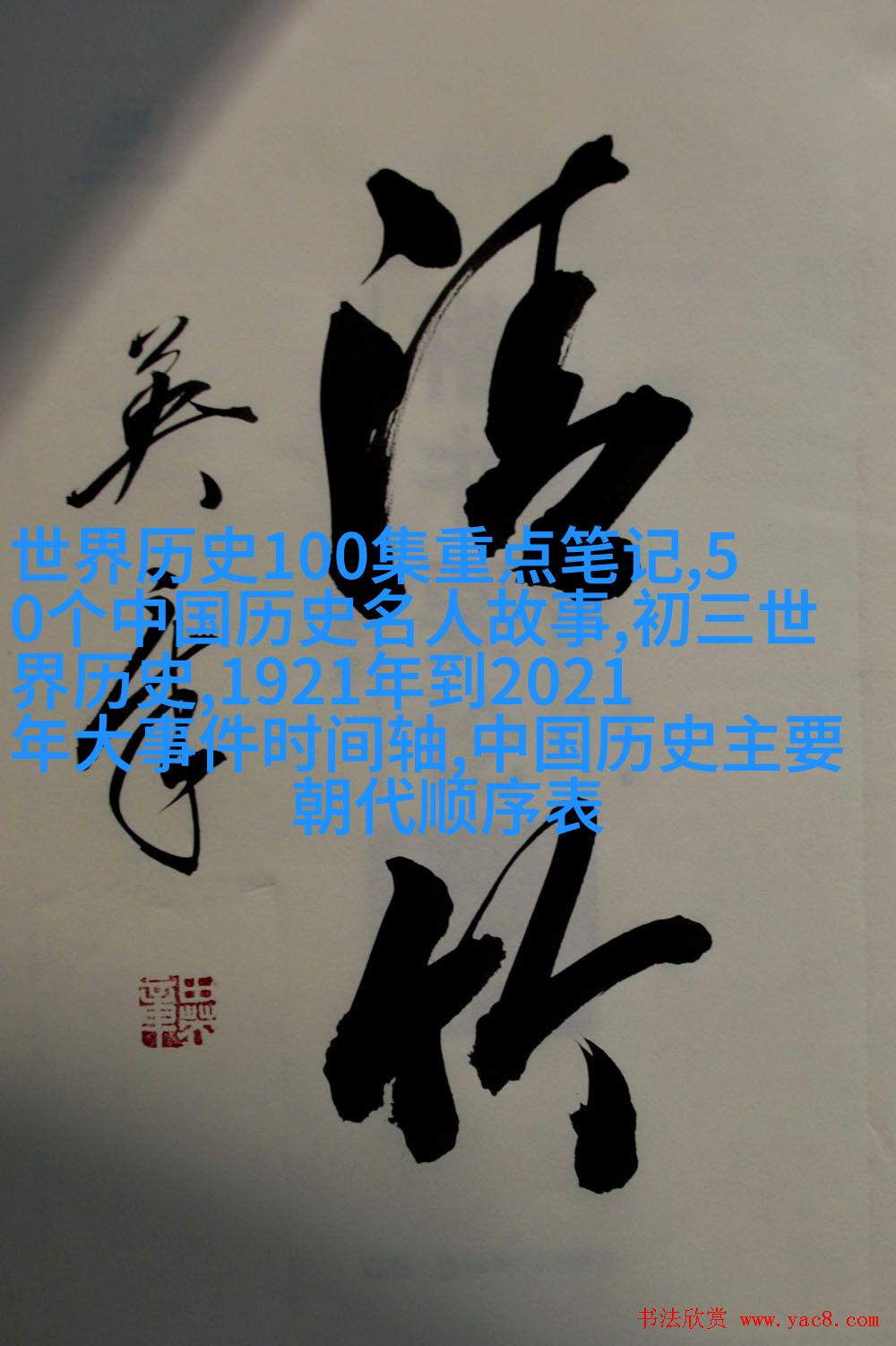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实际上,他们被融入军事机构已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作为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灌输“全普鲁士”心理的工具。由于普鲁士是一个年轻且人为形成的联合体,这使得忠诚于它的情感最初并不自然,因此更需要依靠显著的军事手段来加以灌输。在此过程中,重点内容放在义务、服从、服务与牺牲上。此外,军事美德成为了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较少。

例如,在法国,大约有五万名男性成年贵族,但其中只有少数人经常在军队任职。而在普鲁斯,这几乎是所有容克家族成员都有穿制服参与国家防御的情况。这一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在这个小邦国里,对地主阶级授予官职以及允许他们对农民施行绝对支配权这一现实。
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也像其他专制统治者一样,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个地方议会实行压制。为了平息大土地所有者的不满,统治者允许在军队中对这些人物授予官职,并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如所欲。因此,普鲁士君主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统治者与土地拥有者的谅解之上,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加入他的军队;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这些土地拥有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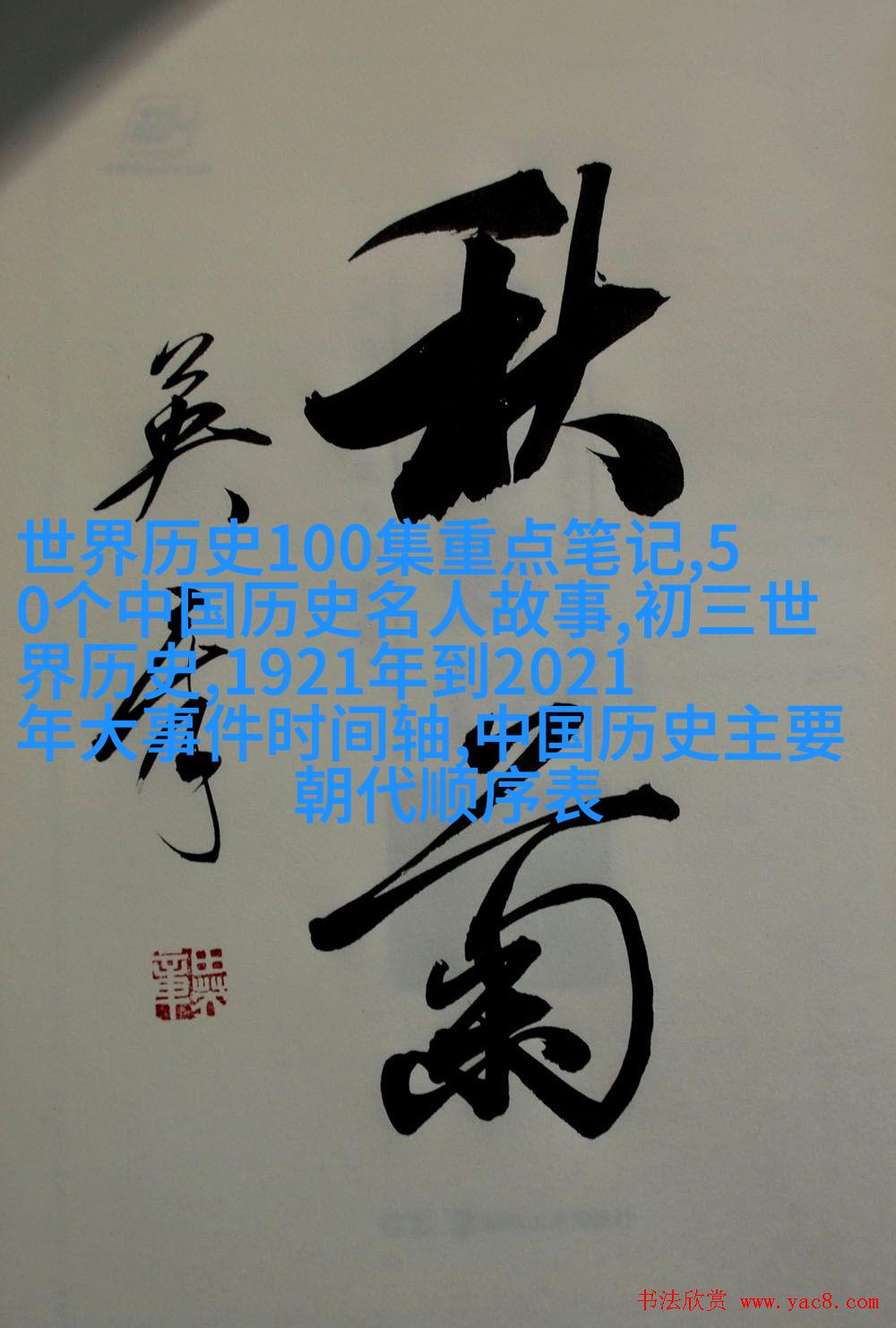
农奴制度在东欧各地区十分盛行,其中包括东部的波罗的海地区,就像波兰一样悲惨。在这种情况下, 普鲁士的地主们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将领,因为他们是在管辖自己的农民习惯中的长大的。此外,由法律规定,不得出售“贵族”土地,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人群,以维护高级指挥官阶层。在法国,则形成了鲜明对比:采邑权利简单转变成了财产形式,使资产阶级乃至普通百姓都能合法取得采邑并享受领主或“封建贵族”的收益。
然而,在普魯西,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由于具有不可变更性的财产形式,每个社会层次被冻结了,因此中产阶级的人很难通过担任当时可获得的地主工作而进入高门阀圈子。一句话来说,没有独立精神的大众资产阶级存在。而且,在东部几乎没有德意志古老城镇,而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因为这里的人口相对于其他地方要贫穷很多,只有极少量私有的财富可供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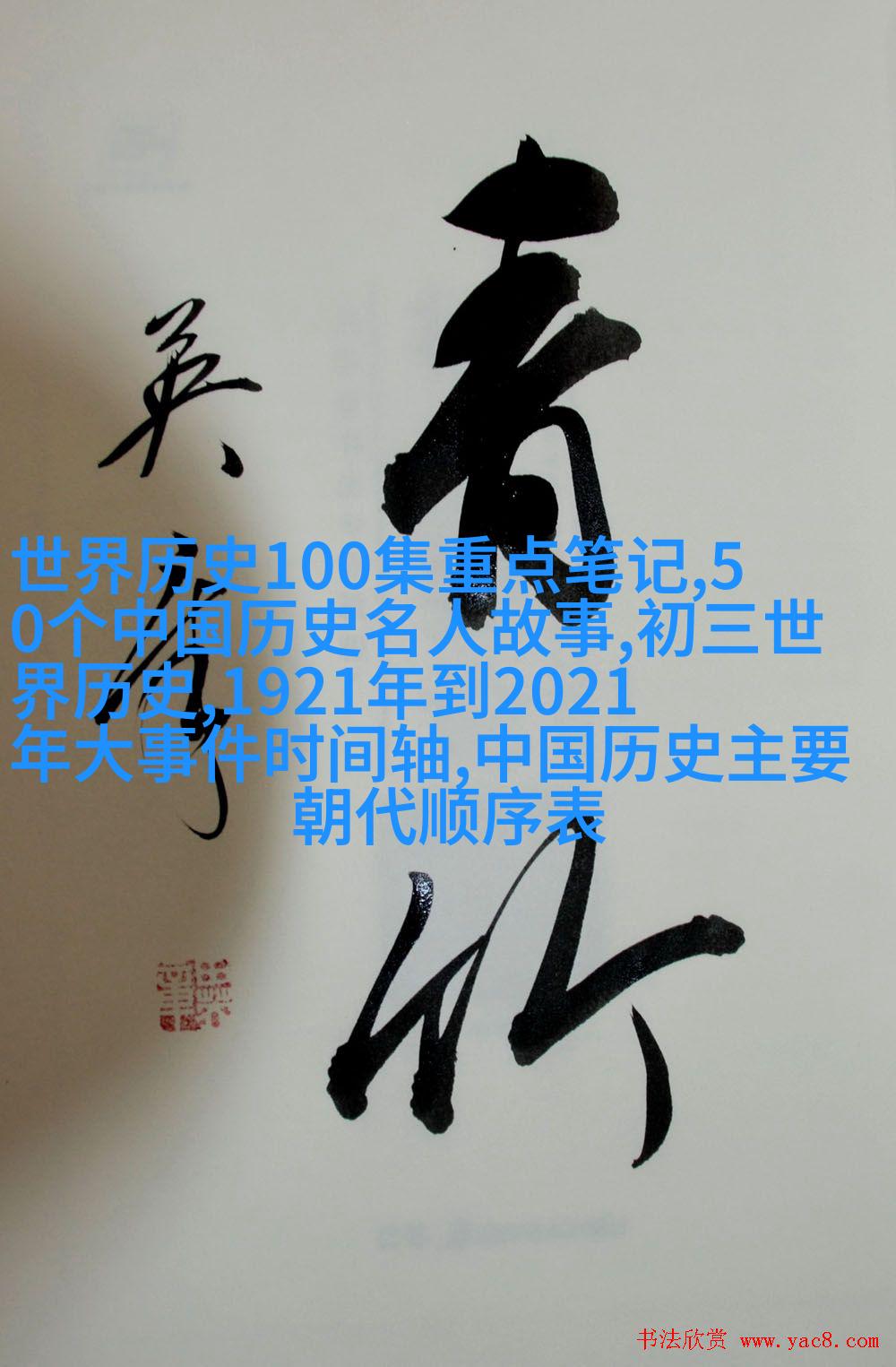
典型的是文官,他代表政府工作,或是管理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赖国家津贴维持企业运作。他还负责处理各种租借合同,一直到他掌握全部相关细节,从而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的行为和决策方式都是由这个传说般的地方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传递过来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即位期间,这些特质得到进一步强化。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且粗俗的人物,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情,而他的父亲和祖父,以及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帝)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非常吝啬,将皇家开销减少四分之三,只花两千五百四十七银币去举办一次加冕仪式,而他父亲曾花费五百万银币用于同样的场合。这位君王就像一个德意志父亲那样执着于国家事务,与个人私宅相同严格监督每一点,每天工作至晚,还希望每个人都跟随他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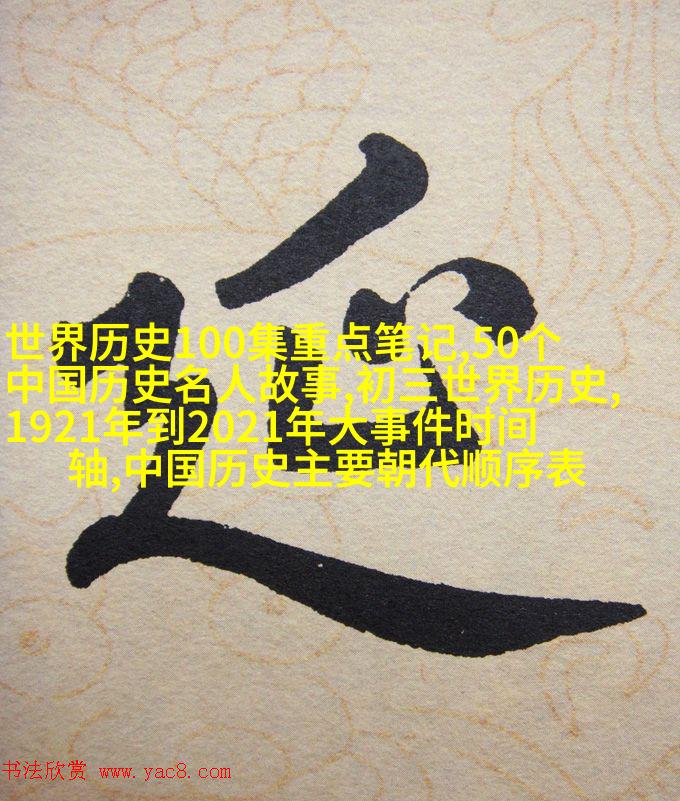
他热爱其陆战力量,他创立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支持它。他是个永远穿着露面的第一个布朗登堡-安斯巴赫家族成员,并重新安排宫廷礼仪程序,让文官处境艰难而尊敬武力。他特别钟爱身材高挑的大兵,为此成立了一支由来自世界各地巨帆兵组成特别团——甚至彼得大帝送来了几名亚洲巨汉。但他也推出了新的训练方法和演习规程,并建立了一所培养容克少年学员的地方学校,以及一种招募制度,它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团都会有一定的区域或者州作为其兵源区(这种招募方式在地球历史上一直最有效)。
到了他去世时,其陆战力量已经增至八万三千人,那时柏林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达到十万以上的小镇,其中二万人就是陆战人员——这是地球任何城市未曾见到的比例之一。而他留给继承人的不是空洞的话语,是真正金钱价值七百万银币的手头资金——尽管实际战斗经验不足多余零星,因为即便如此,也足够让欧洲震惊不已。当奥匈帝国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宣布她继承查理六世遗留下的诸多权利时,全世界皆期待,但就在其他国家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开始进攻。她既未发出警告就调动其部署进入西里西亚,也无需提醒便调动其部署进入波希米亚北边界附近勃兰登堡王国边界附近,有关霍亨索伦家族旧日要求过则隐晦模糊不过透露及暗示某些关于过去领域控制扩张原则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