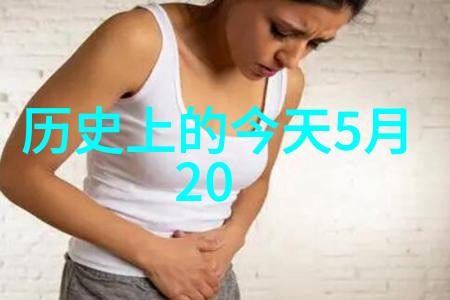五四运动后,现代汉语语境下最早使用“通识”一词来深入讨论大学教育问题的是钱穆的《改革大学制度议》(1940年)和梅贻琦与潘光旦的《大学一解》(1941年)。当时中国已经参照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大学,知识分子也已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关心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一方面体会到西式专业分科的大学体系“将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古今之全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危机,同时也觉察到美国大学正在兴起源自西方古典精神的GeneralEducation改革。出于对汉语的娴熟,他们自然而然地以“通”对“专”、“识”对“业”,创造性地使用“通识”这一概念,从中国古典而非西方古典中汲取思想资源来补完现代大学理念。

半个多世纪后,中国高校终于有条件、有能力将这种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探索。21世纪初,在“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各种名义下,中国高校陆续开启了实质上相近似的改革实践。如今,越来越多人对这种不把教育局限在专业之内,旨在健全育人的教育理念有了大体的认知和认同。然而由于命名交错,实践近似,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总要借助GeneralEducation、LiberalEducation、LiberalArts等英文概念来比附其意义,不免造成了一些混淆,也导致本应内生驱动的教育改革不得不建立在外来概念之上。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中国高校大范围实施通识课程改革始终萦绕着关于"通识"名称及其内涵争论。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通"字及"智"字在中文文献中的用法,并结合人物对于这两个字含义的心得感悟,以期为当前实施的人文学科修养课程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通”的含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地理或物理上的连结,它更偏向于一种理解力或洞察力的象征。在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和变革之后,这种理解力成为了区别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关键桥梁。而且,“智”的运用同样丰富多彩,它可以指代一种独特的情感反应,或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更常常被赋予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心灵状态——能够洞察事物本质。
因此,当我们谈论传统士人的人格理想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智慧”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跨越时间、空间,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正是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中,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能够适应复杂世界环境的人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引发更多关于如何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源,如世界历史大事年表书籍,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训练,以及如何让这些资源更加贴合当下的社会需求,从而促进学校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我认为通过不断深入研究并探索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和个人成长,并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和创新性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