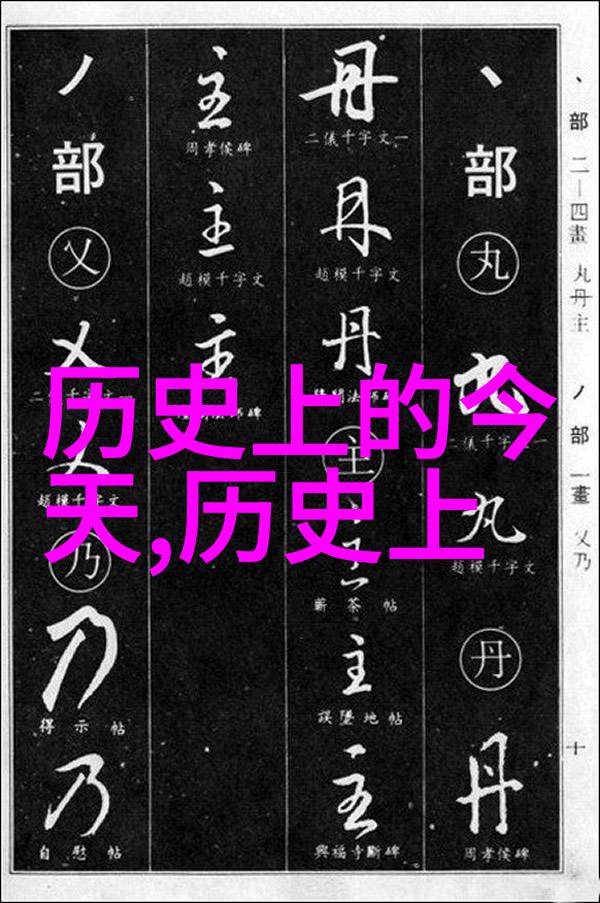五四运动后,现代汉语语境下最早使用“通识”一词来深入讨论大学教育问题的是钱穆的《改革大学制度议》(1940年)和梅贻琦与潘光旦的《大学一解》(1941年)。当时中国已经参照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大学,知识分子也已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关心高等教育的有识之士一方面体会到西式专业分科的大学体系“将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古今之全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危机,同时也觉察到美国大学正在兴起源自西方古典精神的GeneralEducation改革。出于对汉语的娴熟,他们自然而然地以“通”对“专”、“识”对“业”,创造性地使用“通识”这一概念,从中国古典而非西方古典中汲取思想资源来补完现代大学理念。

半个多世纪后,中国高校终于有条件、有能力将这种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探索。21世纪初,在“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各种名义下,中国高校陆续开启了实质上相近似的改革实践。如今,越来越多人对这种不把教育局限在专业之内,旨在健全育人的教育理念有了大体的认知和认同。然而,由于命名交错,实践近似,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总要借助GeneralEducation、LiberalEducation、LiberalArts等英文概念来比附其意义,这造成了许多混淆,也导致本应内生驱动的教育改革不得不建立在外来概念之上。
其中,更为突出的是中国高校大范围实施的通识education改革始终萦绕着关于“通識”的名称及其内涵的大量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场关于何谓真正的人类主义与全面发展的问题,并从德国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或人物身上寻找答案。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期,当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变革,而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学术与新时代之间关系的时候。在这个转型期,一群德国哲学家,如赫尔der林(Hegel)、费希特(Fichte)和舒勒(Schelling),他们试图通过哲学去理解并指导社会变革。这是他们对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适应快速变化时代的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了新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可以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一批德国教授,如威廉·冯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奥托·格吕克克(Otto Gruppe),他们致力于创建一种整合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心灵成长课程。这段时间里,对于如何培养跨学科合作能力以及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最后,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中叶以后,即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时期,在哪些方式被用以确保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怎样利用教书作为工具去塑造公民身份。而此过程中,“通識”的角色又是怎样的?它是否只是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内容出现,或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扮演核心作用?
通过以上几个阶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德国历史背景下的通識education概念,并探索其如何影响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学环境。此外,从不同人物身上看到这些思想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需求而进行调整的人文主义传统,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追求,更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实现的人类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