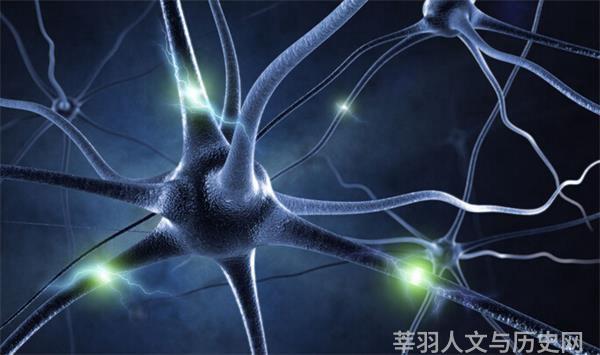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佛道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佛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译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师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译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谶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儒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关系。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同时并存,各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