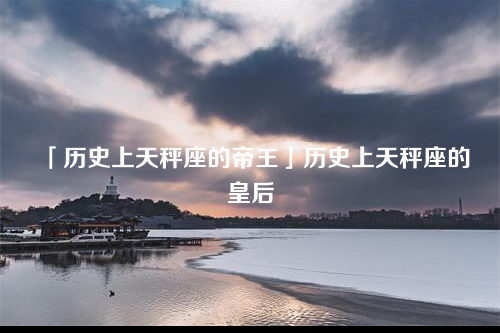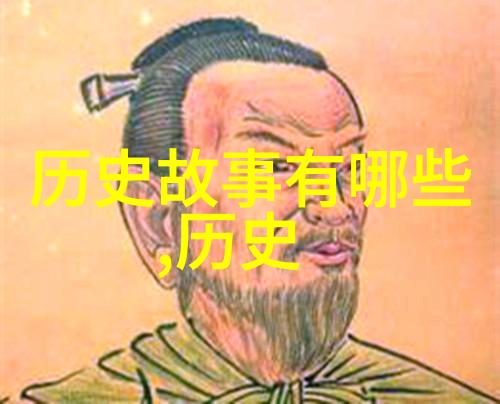清朝乾隆年间,扬州出了个有名的文人,叫汪中。汪中小时候家里很穷,无钱供他上学。他天资智慧,全靠勤恳自学。
汪中的记性极好,不管什么书。过目不忘,没有钱买书,他就跑到书坊里找书看,一目十行。他一文不花,就把那本书由头至尾统统记到肚子里去了。书店的人笑称他为”书癫”,又夸他说:”无书不读是汪中。”
江中家里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隔邻开茶楼的王老二伴侣俩可怜他,就在茶楼店堂的角落里留个地方给他看书,汪中一坐就是一天。茶楼交易兴旺,嘈杂声不绝,汪中不在乎,他读他的书。店堂里常有人赊欠,有钱人和熟人喝过茶,都只记笔账,到年尾一总把钱,一年记下来,茶楼的流水账就是厚厚一大本。
那一年年尾,王老二照例把账册归拢装订好了,放到账桌上,准备第二天向赊账人收钱。不想半半夜老鼠碰翻了蜡烛台,把本厚厚的账册烧得一于二净。账桌也烧了个大洞。等到王老二起床扑救,只剩一堆纸灰了。想想一年白辛苦,老伴侣俩抱头痛哭。哭着哭着,王老二的妻子突然想起说:”人家都说汪相公记性好,他每日在店堂里念书。作兴每日听到你记账的数目哩。”一句话把王老二提醒:”对呀!每日记账时,我都要大声报一遍,某某人今天上账几文,让客人核对,说不定汪相公记得哩。”那时就把汪中请来。汪中一听,笑了笑说:”小事,小事,莫烦,莫烦,我报你重记。”
汪中就从当年正月初五茶楼开业报起,张三某天几文,李四几文,王五几文,某天赵六几文,周七儿文,一口吻报到腊月二十六,没有一笔记错、遗漏的,真是清明显楚,明明白白,三个铜钱摆两边–一是一,二是二。竟和本来记的账一模一样。当天,王老二把账记好,第二天照常收钱,一文不差。本来汪中眼观六面,耳听八方,每日读的记到肚里去了,茶楼里的小事他也留神,没想到今天帮了王老二的大忙,你说汪中记性神不神?
一传十,十传百,汪中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把扬州城能找到的书都看了一遍。又出去游历了一段时间,遍访海内奇书,珍本秘笈,无书不看,又遇名师贵宾指点,学问大有上进。但他不愿应试做官,又不会干另外谋生,啃书不能当饭吃哪!想来想去,就在家门口挂了个招牌。”修补全国残书”,专门修补世上的书,珍本书。因为他学识渊博,才气过人,主顾盈门。
一天,天上的魁星驾云经过此地,突然瞥见扬州三街六铺的众多招牌之中,隐隐露出六个大字:”修补全国残书”。魁星冷笑了一声:”好大的口吻!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立即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挟着一个满是尘埃的青布包,来找汪中汪中问:”老丈有何赐教?”
魁星说:”老夫祖传古书一部,束之高阁,百十余年,不想虫蛀鼠咬,不成容貌,烦请先生修补。”说着打开青布包,负担里裹着个破旧书匣、再打开书匣一看,汪中不由暗吃一惊:这哪里是本书?分明是一堆烂纸片,这些纸片有的蛀得成纸屑,有的霉烂粘在一起,分不开,拿不起。汪中轻轻从纸堆中拣出两块稍大点儿的纸片,仔细一看,笑着说:”老丈不必心烦,此书乃数年前一位高人所作,传世仅有两册,所幸小生曾见此书的另一册,抄补尚可复原,老丈且请坐候。”
汪中立即埋头默写起来,不消几个时辰,汪中就抄补完毕。魁星一看,心里暗暗称赞:果真名不虚传,他交了补书费,出门化为一阵清风走了。魁星还想试一试。过了一天,他又来了,这次他化为一个年青秀才,用仙术变化成一部几种古书拼凑起来的宋版书,上门求补。汪中方才起床,一见来了客人,便问什么事。秀才说:”祖传孤本宋版书一部,数日前正想展读,谁知被书童不慎烧去数页,闻先生修补全国残书,故此千里登门求补。”说着,把书奉上。汪中接过书一看,倒也真像是宋版书,纸张,印刷、装订、款式无一不像,书中有几页被烧残、再看文字、以为似曾相识,但又似是而非,记不得是本什么书了,这在汪中仍是第一次。
汪中说:”我刚起床,尚未梳洗,客人先请用茶,稍待片晌我就来修补。”汪中进房洗脸,一边洗,一边想,仍是想不起来。
怎么办呢?汪中请秀才一道用早点,存心拖延时间,一边吃,一边想,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回忆了一遍,仍是对不上号。看看早饭已经吃完,汪中自己也有些急了。
秀才不耐烦了,起身对汪中说:”我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不想先生名存实亡,让我空跑了一趟,我只好另请高超了。”那时就要取书走路。汪中重复推想,断定这部书是今人拼凑的古人作品,假借宋版书名义来为难自己。汪中说:”先生此书算不得奇书,不过是今人拼凑古籍的杂烩罢了,不过书能乱真到此,也难能难得了,原书送上,还望鉴谅。
哪晓得秀才听了,非但没有气愤,反而哈哈大笑,连声称赞。”汪先生名不虚传,服气、服气!”说完,用手向门口的”修补全国残书”的油漆招牌一指,说也希奇,那招牌立即金光闪闪,变成一块金字招牌,愈擦愈亮,永不退色。秀才也随之化为一阵清风,不见了。
汪中的名气终于传进了都城,连乾隆帝王都知道了。那时帝王正召集全国名士编修四库全书,当然不愿放过这个大才。也把汪中请去加入编纂。今天,我们看到那规模弘大的四库全书时,不要健忘这里面也有汪中的一分功劳哩!